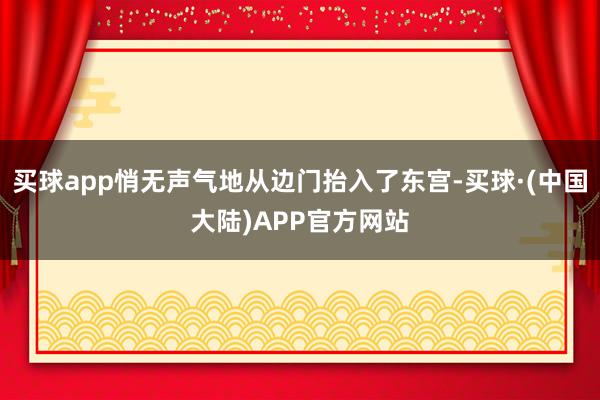
我自小便知买球app,我改日是要作念太子妃的。
可大婚当晚,太子萧皆安却有益走错婚房,和皇后身边的婢女青柠圆了房。
青柠是皇后身边最得宠的婢女,曾替皇后挡过一刀。
因此,皇后也只气了顷刻,便点了头。
我爹娘就地大怒,我谢家手捏七十万兵权,岂肯受这般挫辱?
他们思闯宫门,求圣上作念主。
我却轻轻拉住他们的袖口,劝他们忍一忍。
当日,我躬行面圣,替萧皆安求情。
“求皇上准青柠入东宫,全了太子的情意。”
一个宫女汉典,我还不至于放在心上。
他心不在我,我亦不曾动心。
我要的,从来不是萧皆安这个东谈主。
而是太子妃的尊严,改日的后位,和谢氏一族的永世新生。
我替太子求情,准青柠入东宫的音信,不出半日便传遍了宫廷表里。
伸开剩余87%世东谈主反映互异,大抵都笑我谢家女儿还未封爵,便先学会了委曲求全。
唯有父亲在听到我让知友带回府的“按兵不动,静待后赏”八字后,千里默了半晌,终是压下了整个部将的愤愤抗拒。
三日后,圣旨降下。
太子妃封爵礼已经,而青柠,则以良娣的身份,在同日由一顶小轿,悄无声气地从边门抬入了东宫。
封爵礼庞杂宽敞。
我身着繁复安详的太子妃冠服,在文武百官的醒目下,一步步走上汉白玉阶,从礼官手中接过金册宝印。
萧皆安站在我身侧,他面目俊朗,身姿挺拔,是天家最完整的储君神情。
仅仅投向我眼神里,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注目与冷意。
我迎着他的视野,微微弯起唇角,露出一个恰到平允的温婉笑颜。
他大致在奇怪,我为何不哭不闹,甚而亲手将他怜爱之东谈主送到他身边。
他不懂,我要的,从来不是他那点带着调停的怜爱。
礼成当晚,他居然莫得来我的寝殿。
侍女云舒替我卸下钗环,口吻未免带上几分不忿:“太子殿下他……终究是去了青良娣的揽月阁。”
铜镜中,我的眉眼瓦解依旧,莫得半分浪潮。
“下去吧。”
殿内烛火摇曳,只剩我一东谈主。
我走到窗边,望向揽月阁的标的,那里灯火通后,思必恰是情浓之时。
心头并无酸楚,唯有一派冰凉的统共。
萧皆安这一步走得太急太蠢,他用欺凌我来举高青柠,殊不知,这正值将他和他的心上东谈主,都架在了猛火上炙烤。
一个让太子在新婚夜便失礼、让手捏重兵的岳家蒙羞的“宠妾”,在这吃东谈主的深宫里,只会是一个活靶子。
次日早晨,我以太子妃之尊,危坐于主位之上,罗致东宫一众姬妾的拜见。
青柠来得不早不晚,一稔零丁水红色的衣裙,眉眼间带着通宵春宵后的妩媚,与一点醉中逐月的满足。
她依礼下拜,声气柔婉:“妾身青柠,拜见太子妃娘娘。”
我并未坐窝叫起,仅仅端起手边的茶盏,轻轻拨了拨浮沫,眼神安心性扫过她微微胆怯的指尖。
殿内已而静得可怕,整个姬妾都屏住了呼吸。
顷刻后,我才逐渐启齿,声气饶恕却带着禁绝置疑的威仪:“青良娣请起。你既已入东宫,往后便需恪守端正,精心服待太子,为皇家开枝散叶才是正理。”
我赏下了一套赤金头面,与整个侍妾一般无二,既全了她的体面,也绝了她思借此彰显特殊的念头。
她接过奖赏,谢恩时,脸上那抹满足终究是淡了下去,洗心革面的是一点严慎。
我看着她,心中冷笑。
萧皆安大概能给她宠爱,但我手捏的,是名分,是端正,是这东宫女主东谈主的权力。
他给的宠爱是活水,而我捏在手中的权力,才是铁打的营盘。
几日后的宫宴上,皇后特地将我唤至身边,拉着我的手,口吻带着几分安抚的意味:“好孩子,委曲你了。皆安他……仅仅一时蒙胧。”
我垂下眼睫,姿态恭顺:“母后言重了。太子殿下至情至性,是国之幸事。青良娣对母后有救命之恩,儿臣理应善待。”
“儿臣既为太子正妃,自当事事以殿下为重,以东宫沉静为重。”
皇后看着我,眼中掠过一点委果的吟唱和消弱。
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容东谈主、识大体、能稳住样子的太子妃,而不是一个争风俗愤、搅得东宫不宁的妒妇。
回到东宫,夜已深。
云舒为我披上外衫,柔声谈:“姑娘,您当天在宫中……何不顺势让皇后娘娘……”
我抬手止住她的话,走到书案前。
案上,正摆着那枚属于太子妃的宝印,在烛光下泛着温润而冰冷的光芒。
“云舒,你看这宝印,”我轻轻抚过上头邃密的凤纹,口吻日常无波,“它代表的是权力,是地位,是谢氏一族的荣辱。至于太子的心在谁那里……”
我抬眼,望向窗外千里千里的夜色,唇边溢出一点极淡的弧度。
“与我何关?”
暮色渐千里,东宫的红墙映着临了一齐残阳。
自青柠入东宫已有三月,萧皆安的确再未踏足我的寝殿。
日间里他尚保管着太子应有的体统,与我一同入宫问候、出席典仪。
可一朝回到东宫,那双眼睛便只追着揽月阁的标的。
宫中坏话渐起,都说太子妃空有尊位,实则连太子的一派衣角都留不住。
我浑不介意,逐日依旧迁延阻挡宫务,去坤宁宫向皇后问候也从不牢骚,只将东宫账目、费用安排得了了妥帖。
皇后起初还宽慰几句,自后见我这般“不争光”,眉宇间也未免染上几分发火——她不错容忍男儿一时情迷,却不可容忍东宫历久无嫡。
时机,差未几了。
这日晌午,我正于水榭赏荷,云舒悄步近前,柔声谈:“娘娘,事情已安排适当。青柠良娣的兄长,前几日在西市‘偶遇’了永昌伯家的三令郎。”
我捻着鱼食,夷犹未定地撒入池中,引得锦鲤争相跃动。
永昌伯府的三令郎,是京中驰名的纨绔,尤好斗鸡走马。
青柠那兄长,自妹妹得宠后便飘飘然,最受不得激将。
几句“国舅爷岂能不会此谈”的谄媚,便足以让他昏头昏脑。
“马场那儿,可都打点好了?”
“万无一失。那匹马动过行为,跑不出半圈必惊。永昌伯三令郎身边的小厮,也都是‘我方东谈主’。”
我微微颔首。
不外两日,凶信便传入了东宫——青柠兄长与东谈主跑马,马匹蓦地受惊,不仅将他摔成重伤,还冲撞了恰在隔邻散心的康宁长公主的仪驾。
长公主受惊凤体违和,陛下闻讯大怒。
揽月阁内顿时哭天抢地。
青柠跪在萧皆安眼前,梨花带雨地求他救命。
萧皆安当然思保。
可此番牵涉到皇室长者,又凭据可信,他刚在御前启齿,便被陛下厉声斥回:“为了一个妾室的兄长,你竟要两袖清风,插手你的皇姑母?萧皆安,你的储君之谈呢!”
他被禁足东宫,无诏不得出。
风雨欲来。
我依旧逐日去小佛堂为长公主祝颂,抄写经籍,仿佛外界浪潮与我毫无干系。
三日后,坤宁宫来了东谈主。
皇后娘娘凤颜含霜,将一纸诉状掷于地上——那上头陈列了青柠兄长仗着东宫势力,强占民田、纵奴行凶的诸多短处,苦主联名上书,直递到了御史台。
“太子妃,”皇后娘娘的声气带着无语与冷意,“你可知罪?”
我坐窝跪伏于地,口吻惊险却瓦解:“母后息怒!是儿臣渎职,未能阻挡东宫家族,致使良娣兄长行差踏错,损及天家面子……儿臣愿领解决。”
我认错认得干脆,将整个职守揽到了“阻挡不力”上,绝口不提青柠。
皇后凝视我顷刻,神情复杂地挥挥手:“起来吧。此事……也怨不得你。”
她怎么不知根源在谁?
恰是我的“窝囊”与“素丽”,反衬出揽月阁的不知进退,和太子的恣意偏宠。
【点击这里 搜检后序】买球app
发布于:江西省